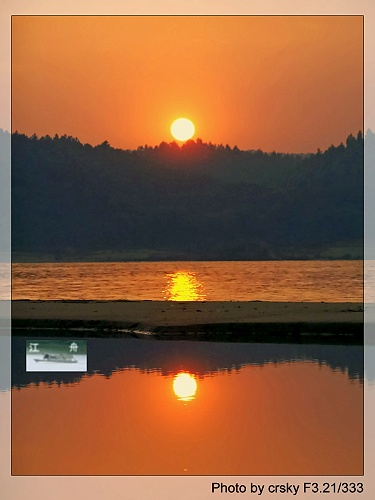[NextPage世纪50年代初的博罗县城]
罗阳镇位于博罗县境南部,东江中下游北岸。东部、南部与惠城区接壤。公元503年(梁天监二年)始为县治所在地。时因城內多有大榕树,故有榕城之称。解放之后称为“城镇”,当时城镇面积约为0.5平方公里,人口2万人。

(此榕树位于葫芦岭铁炉巷內,据说有四五百年树龄,被列为县级保护文物)



1986年,又因县城在罗山之阳,在撤销原附城公社合并于城镇时,更名为罗阳镇。2004年义和镇并入罗阳,罗阳镇面积达384.8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
[NextPage“传说中”与现实中的古城墙]
“传说中”与现实中的古城墙
完整的罗阳古城墙,只有我们的祖辈才见过。
罗阳成为县治时只是一个小圩市。1365年环城始筑土墙(沿江立木栅),经元明清三朝完善,至清末,城周5里,高2丈4尺,厚一丈,雉堞2737个,城门10座,即东门(广仁)、小东门(安阜)、南门(文治、景星、大南、应骊、忠勤)、大西门(矩关)、小西门(乐成)、北门(太平)。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荡平盘踞在东江、韩江流域的陈炯明叛军。为防止日后据城作乱,民国政下令折毁罗阳城墙。50年代,县城因城建用砖需要,政府动员群众深挖城基砖石。
现在仍存的古城墙仅有葫芦岭东南麓临江地段(旧博罗中学内)约20多米长的一段。
虽说仅存的一小段古城墙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已不复原貌,城墙之上是博中教工家属区“小南海”,城墙的雉堞早已荡然无存。
古城小东门傍葫芦岭而筑,由更鼓前(巷名)可东出九村。1963年,政府建造葫芦岭景区,在小东门的残墙上加建水泥桥,将东北路与葫芦岭东段石级相连。至今,车辆上葫芦岭必经此桥。
北门河因由东向西流经古城北门而得名,也是所谓的“新城”与“老城”的分界线。古北门早已湮没,留下的唯有一座几经扩建的“北门桥”。
[NextPage大江、码头]
大江、码头
论到我对地方上的眷恋,感情最深的非东江莫属。
大江不仅哺育了世代罗阳人,而且还是罗阳的交通命脉。自宋代开始,大江的航运已相当发达,而陆路交通至近代才略有改观,罗阳乃至整个博罗县客货运输主要依赖大江船道,古时官员赴任离任都是在原大东门码头(原博中江段)上落船的。据老人家说,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丰江、枫树坝水库尚未兴建时,从罗阳开出的客货船上溯可达河源、老隆(今龙川)、下延石龙、广州。至80年代初,大江上仍船来船往,不时还见从上游山区县顺江漂流而下长达几百米的竹排、木排(最低成本的运输手段),而负责放竹木排的三两个人就在排上做饭和睡眠。
我清楚的记得,1975年7月我头一回出远门到广州。上午11点多钟,老爸老妈带着我从老城的博罗港客运站码头坐船,晚上7点钟到广州,要在船上住一夜,次日清晨在广州长堤码头上岸。1979年春节我随朋友探亲第一次到惠州,从罗阳坐船花了大概一个半钟头到了桥东码头,回程快了约半个钟头。
到90年代,东江客运彻底停航,货运锐减。剩下的基本上是。。。抽沙船、运沙船!!!!!!!
昔日的东江客运站已变成食肆
都准备好了?尽情地夜游吧!不过小心得了“夜游症”。呵呵!
[NextPage洪水、堤围坣]
自古以来东江流域三年二涝(当然不乏干旱的年份),这种自然灾害自近代以来逐年减少,这主要功于水利建设的成就(包括大中型水库、排灌渠站和堤围)。客观地说,历代洪灾给东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产生命损失,但同时也造就了广袤肥沃的两岸冲积平原,为现代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少好处。
解放以来,东江发生过1959年、1966年两次特大洪灾,罗阳当然未能幸免。据老辈说,这两场洪水以1959年6月那场最大,县城水位15.68米,超过警戒水位4.48米,洪峰流量每秒1.28万立方米。老城内除葫芦岭脚下个别高处,全城房楼淹顶,街道可行舟,大树梢上爬满蛇虫,居民被疏散到山岗上避难,部队出动橡皮艇抢险、出动军机空投赈灾粮食物资。灾后城内余泥及膝,足足清除了两个月。
1959年灾后,政府将老城原有低标准江堤拆除,向江边前移几十米另筑石堤(老城人惯称之为“堤围坣”),沿堤围坣一线拓建了河唇路。堤围坣高约4米,坣顶宽约1.5米,附坣建有多处排洪机房,包括博中校门在内,一共有开设有8个闸门。
就这样一条不足一公里长不起眼的堤围坣,几十年来来默默地拱卫着县城,一次次的抵御着东江洪峰。不清楚东江洪涝史的年轻人,或许会认为它是多余的,觉得它有碍县城观瞻。但依我认为,堤围坣不仅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政府应加大对它的维修加固力度,确保避免类似1959年特大洪水给县城带来的“灭顶之灾”。

堤围坣上望江。我小时经历了在坣顶上爬行、行走、奔跑追逐的成长过程。
由于老城实在狭小,历史上造成约有二千居民居住在堤围坣外的 江沿,众多破旧的房屋现成了一条令人不堪多望一眼的“滨江路”,而这些居民长期以来深受水患之苦,与堤内居民仿如身处两个世界。
我自懂事以来,印象中堤围坣几乎每年都会因洪水闩闸一两次,洪讯期间的正常航运停顿。据住在堤围坣外的居民介绍,最近的一次闩闸是在1992年。

闸门,闩闸是根据江水位往木槽中加放栅木,再往两面栅木之间充填沙石。
我出生以来,只经历过1979年、1983年两次洪水漫县城,但灾害程度远逊于上述的两次洪灾,而没有石堤的对面水一片则成泽国,在城内见到军方直升机不时往对面水空投粮物。值得一提的是,县城这两次水灾均是內涝,仍然是堤围坣抵挡住东江水漫城。
县城东江两岸的景观改造是迟早的事情,只要能确保罗阳免于水患,到时堤围坣也就算完成了它的史命,再让它功成身退吧!
[NextPage对面水]
老城人惯将东江称为“大江”,将东江南岸罗阳所辖的橫坑、翠美园和巷口三个村委会合称为“对面水”。
对面水(橫坑、翠美园、巷口三村委)原属惠阳县潼湖人民公社下属的三个生产大队,它与潼湖其他地方被大山所隔,公社在管理上十分不便;它虽与惠城下角相连,但惠城不肯接纳农村人口。上世纪60年代,对面水划归博罗县附城人民公社,现属罗阳镇管辖。
与归惠阳隔山不同的是,对面水归博罗却隔江。在罗阳东江大桥未落成的近40年间,在县城与对面水之间的机动船(习惯上称为“橫水渡”)成了两岸往来的唯一交通方式。船票从1角、2角、5角涨至断渡时的1元。
当年坐橫水渡
几十年以来,对面水人每逢3、6、9日到县城赴圩集卖土产和购买日用品,生产的大量甘蔗则就近运往惠城下角糖厂。县城人习惯到对面水的河滩上游玩,80年代以前,城内成年人经常到对面水山上割草用作家中燃料,小孩在暑期到山上摘山稔解馋。当时每逢清明时节,对面水人捕捉一种俗称“黄虫”的有翅昆虫到老城摆卖,每只卖1分钱,简直是孩子们的宠物。
90年代初将对面水纳入县城规划的蓝图可谓宏大,至今却未见有动作。罗阳东江大桥通车了,横水渡已成为历史,但现实离县城经大桥直通潼湖的构想仍相距甚远。只要对面水仍属罗阳,对面水是县城拓址的必然选择,时间上的早晚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规划得当,千万千万不要重蹈80年代县城拓址规划上的覆辙!天阿公保佑!!!
[NextPage东江水上人家--疍家]
东江水上人家--疍家
水上人家
谈论东江,疍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
由于我对疍家的认识不多,在此摘录着报刊资料供大家参考:
东江,珠三角的母亲河,全长562公里,由北向南流经江西赣州、广东梅州、河源,然后从惠州穿城而过。而惠州早在隋唐时就有“粤东重镇”之称,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千百年来,惠州人民在江边繁衍生息。在这里,有许多倚江而生的不同群落:他们或以捕鱼为生或以搬运过活;或缝缝补补或沿街叫卖。他们随江水涨落而迁徙,他们的生活因时代发展而翻滚激荡,却始终与东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较完整的东江群落生态原图。
疍家是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以船为家的渔民,种类颇多,可大致分为蚝疍、珠疍、渔疍三种,蚝疍采蚝,珠疍采珠,渔疍在内河捕鱼,东江的疍家人应属渔疍。
走在桥东老街的东江边,总能看到一些小船,或停靠江边修葺,或在江面疾驰,或在水面捕鱼捞蚬……他们就是世代居住在江河上的疍家人。
走进一户疍家,小船里铺着一张凉席,主人平常吃饭、睡觉全在这里。他们生活简单,没有正规意义上的电器,唯一称得上用电的,算是棚墙上挂着的那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了。
桥东码头附近的疍民绝大部分来自广西梧州。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梧州顺江而下来到这里,一直靠捕鱼和捞蚬为生。他们将船驶至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地方捕鱼捞蚬,然后返回桥东码头附近岸上的市场交易。6、7月份,是河蚬最多的时候,大一点的蚬可以卖到两三块钱一斤,运气好的一天能捞两百元甚至更多。但过了这两个月,河蚬就少得可怜。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电鱼、炸鱼,江里的鱼越来越少,疍民的生计也越来越艰难。
“可我不愿意上岸,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我还是离不开这船。”40多岁的老倪说。他有着疍家人的典型特征:皮肤黝黑,手臂强壮,脚掌宽厚,脚趾比常人张得更开,这是长年行船造成的,这样子使他在船上站得更稳。他的两个小孩要上学,在岸上租了房子住。“晚上我总要回到船上,船板上睡得踏实,这么多年都在船上,要是没有点摇摇晃晃的感觉,还真不习惯。”
傍晚将至,一些渔船捕鱼归来,男人忙着收拾渔具,修补渔船;女人则连忙在船头泥炉上烧柴做饭。袅袅炊烟在浩淼的江面上缓缓地升腾……(南方都市报)
疍家打渔人老刘
“用电啊、炸药啊那些东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最终害的还是自己”
在横沥镇探访东江时,江上的几条小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岸边的村民告诉记者,那是附近的水上村的渔船。经过费力的呼喊,记者终于与一条渔船上的人搭上了联系,经船家允许,记者踏上了这条渔船。船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姓刘。老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水上村是横沥镇惟一的一个渔村,村里的人几乎全部靠在东江打鱼为生。水上村的人原本都是疍家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水上,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政府的上岸政策才上了陆地变成了村民。老刘说,他在东江上生活了一辈子,早已离不开这条江了。
老刘告诉记者,“从十多年前开始,鱼就一年比一年难打,那时候打鱼一天能挣30多块钱,现在只能挣到一半的钱。不是东江的水变差了,而是鱼变少了。”老刘说,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的打鱼人都采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用电击,用炸药,打的鱼又快又多,而水上村人一直坚持用渔网。“并不是我们不会用这些东西,可用电啊用炸药啊那些东西,大鱼小鱼一起被炸死,江里的鱼越来越少,最终害的还是自己。”(南方都市报)
大年初三,午后的海南省陵水县新村港,栉比鳞次泊着几百艘回港的渔船,在耀眼的阳光下煞是壮观。船桅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船身上各式各样的春联、扎捆成堆的白色浮珠和粗大缆绳,无不骄傲地显示着疍家人的富足和豪情。顾不上午休,船上的男人女人或外出会友,或邀客上船,或杀鸡宰鸭,喧天哗声随微澜的轻波不住向四周扩散……
年逾五十的吴增友跨过几艘渔船,回到自家船上。他刚刚邀了几位平时难得见面的船老大喝下午茶,哥几个聊着海上生活、来年的打算,喜悦和满足涨红了渔家汉子黝黑的脸庞。明天,新村港许多渔船又要离港,开始日复一日的海上生涯。
许是海上生活太寂寞冗长,疍家人对岸的渴望才如此浓烈。和许多渔船一样,大年廿八,老吴一家就打道回港了,在新村港里早早占了好船位。一家人顾不上海上跋涉的疲惫,立即分工准备过年,男人负责张贴对联、买鞭炮,女人忙着打扫卫生、准备年货。相比之下,男人轻松多了。在勤劳的疍家女人心目中,在海上男人是渔船的魂儿,到了岸上也该歇口气了。
老吴的灯光围网船是去年新造的,花了80万元,船长24米、宽5米,足够老吴一家和十来个伙计住了。新村港有200多艘渔船,但像老吴这样的新船还不多见。这艘新船是老吴一家的骄傲,即使回港,一家人也不愿到岸上住,今年,老吴用心地把渔船妆扮一番,船头船尾整整齐齐贴着一排红联,写满了“接福迎春”等喜庆字眼,驾驶舱外墙上则是一幅刚猷有力的对联“大吉大利平安福,新年新景如意春”。小小春联,饱含着疍家人新年的希冀与愿望。
在三亚人民医院工作的小弟吴陈明也回来过年。老吴家有六兄弟,只有小弟彻底告别了大海,其他几个兄弟,要么依旧漂在海上,要么改行围网养鱼。而老吴的两个儿子,也传承了祖辈对海的依恋,日日跟着父亲在海上漂泊。老吴兄弟几个靠着船舷,唠着家常,淡淡烟雾中道不尽人生沧桑百变。几个妯娌媳妇,早早在船头船尾忙开了,炸鸡肉、宰鱼、洗菜、洗衣服、哄小孩……
因为在海上夜间要捕鱼,疍家人养成早吃晚饭的习惯。才4点钟,香喷喷的团圆饭就开锅了。船二楼的舷板上,一口大锅摆在中间,大伙席地而坐,疍家人管这叫“围炉”。吃饭前,老吴在驾驶舱的祖先牌位前,恭恭敬敬地续上香、鞠躬作揖,祈求一家平安、来年有个好收成。在疍家人眼里,从年三十下午起,祖宗牌位前的香火就不能断。
疍家人的团圆饭,当然少不了鱼。刀工齐整的鱼肉盛在一口大脸盆里,烤得清香四溢的鱿鱼、鸡肉让人垂涎欲滴,一种叫“小姐簪”的甜品也炸得焦黄澄亮。老吴说,疍家人终日在海上鲜有肉吃,一靠岸三餐就少不了各种肉食。按疍家人旧时年俗,必须等男人酒足饭饱之后,女人才能上桌吃饭。然而,时代变了,许多疍家的习俗也日渐老去。
明天,老吴的渔船就要驶向文昌一带。这一去,至少又要好几个月才能回到新村。虽是年里,兄弟相惜间仍免不了淡淡的感伤。当一家人欢欢喜喜吃着“围炉”饭,聊着家常,甚至还会面红耳赤地争执上几句,爽朗的话语和笑声,连同淡淡的忧愁,都顺着通透的船舷飘到港里,飘到海上。
斜阳西沉,沐着微微醉人的暖风,疍家人短暂的“年”又该划上一次句号。新村港里的几百艘渔船,又将从这里启锚驶向新的远方。每一次告别,都是对来年的一次期盼,对人生的一种憧憬。春节年年过,令疍家人梦萦魂牵的,是年里浓浓的人情味,是人们心甘情愿在年里沉醉。
疍家人
疍家人,是我国古代南方的水上居民,又称蛋民、蛋家、蛋户等。据说是因为他们长年累月以船为家,如同漂浮于盐水之上的鸡蛋而得名。海南的疍家人主要集中在海口海甸港,陵水新村港,昌江海尾,三亚南边海、保平港、望楼港一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疍家的生活习俗已与岸上的汉族基本同化,过年也不例外。疍民中有不少是信基督教的,但到了传统的新春佳节,同样要裁新衣、买年货,欢欢喜喜过新年;信奉道教和佛教的,更要在他们生活的船上烧香点烛,拜天拜地祭祖宗。
旧时,疍民有“讨斋”的习俗。“讨斋”多在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他们三五成群结伴上岸,挨家挨户地唱诗讨斋。正月初一晚上,岸上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斋,等待第二天送给前来唱诗讨斋的疍民。讨斋的疍民男女,穿着新衣,头戴红花,手挎竹篮。他们举止礼貌,歌喉婉转,操词吉利。送者也热情赠与,十分友好。随着时代变迁,“讨斋”习俗也渐渐远去(海南日报)
清晨的大海,轻雾茫茫,五彩霞光,迎着晨风,一艘艘挂满风帆的疍家渔船又开始一天的劳作。偶尔,可看到一艘船蓬上摆着一盆桔子或花草,那是船主人有意安排的,“子壮未有室,则置果树一盆于蓬;女长未有室外,则置花草一盆于蓬。媒妁凭是议婚合婚。”原来,这都是船家父母为其儿女求婚配的信号。
归船靠港后,有媒人会找上船来,向船家谈论儿女婚配之事,而后双方船只经常停靠在一起,以便使儿女或双方父母增进了解。中意后,男方父母就得准备聘礼,请媒人置一彩船送至女方“家”。彩船装扮得很漂亮,还安排了乐队,吹吹打打的向女方船家开去。疍家人的婚恋习俗家女的身价很高的,衣服、头饰、金簪、玉镯,十分贵重。
迎亲那天,疍家新娘与海南其他汉人一样有哭嫁的习俗,况且要哭得两眼红肿,才显得真诚。疍家的新娘打扮也极为漂亮,着红装,戴凤冠,穿艳丽的袜子但不穿鞋。夜深人静,渔火点点。在媒婆的引导下,在姐妹的护伴下,踏上新郎家摇来的舢板。舢板上披红花巾,坐着新郎的姊姊或大嫂。新娘上舢板时,嫂嫂或姊姊亲自挽扶,表示欢迎她的到来,就这样,这只盛载幸福的舢板开始摇向她的新生活。
新婚的日子新郎倌整天都呆在船家中,布置新家,富有的船主还会为儿子置新船。新娘来到,新郎牵着新娘的手,双双在祖先灵位前拜堂成亲。这时,船民们都会前来祝贺,并燃放鞭炮,热闹非凡。(南方日报)
疍家是对南方水上人家的称呼。整个珠江流域都生活着疍家人。按照蚝疍、珠疍、渔疍的分类,生活在东江的疍家应是渔疍,即以捕鱼为生。
博罗渔业的江河捕捞,可追溯至汉唐时代。《博罗县志》记载的“舟楫为家,捕鱼为业”正是对疍家生活的概括。民国时期捕捞工具多使用抛网、刺网、围网或鸬鹚等方式。1956年全县有专业渔民258户,船333艘,附城区有鸬鹚1110只。
2005年端午节
至近代,东江鱼类资源仍十分丰富。就连在约在三十年前,我经常看到有人划艇在江中炸鱼(多用雷管),一炮可炸得二三百斤鱼。一次见人炸得一条一米多长约有七八十斤的江鱼,两个人用担杆将这条鱼抬走。东江博罗江段有左口、鳤鱼、鳡鱼、大黄鱼、小黄鱼、鳊鱼、舌鳎、马鱼、赤眼鳟、乌鳢、鲚鱼、白凡鱼、鲥鱼(三黎)、刺鱾、花鰶、河豚(俗称鸡泡鱼)。。。太多了,还有河蚌、沙蚬等贝壳类河产。这些历代疍家赖以为生的江鱼,由于近几十年以来,污染、滥捕、水土流失淤塞江河、拦河筑坝切断鱼类洄游觅食或繁殖通道等人为因素,造成大部分种类已几乎绝迹,疍家的鱼获已少得可惜。河鲜的美味毫不逊于海鲜(个人口味),我们越来越难一饱口福了。。。
我们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水枯鱼竭的东江吗?
解放以后,政府对疍家统一管理。博罗县成立了“水上人民公社”,整个东江博罗段的疍家成为公社社员。公社为疍家设置有邻江陆上居所,让他们购买牌价商品粮,小孩在邻近的镇上学校或专门的水上学校读书(我在一小读书时班上有两名疍家同学)。但疍家一家在一小木艇作息的习惯并无改变,个别疍家甚至在艇上养猪养鸡。到80年代初,水上人民公社改制为企业性质的“博罗县水运总公司”,由于不少疍家弃渔上岸另谋生计,全县疍家户数锐减。
游泳是疍家人必不少的技能,无论是大人或小孩。当婴儿到会爬行时,父母会在婴儿的身上绑上浮木做的救生圈以防溺水。小孩到两三岁已会游泳。疍家人比较迷信,他们认为落江溺水的人是天意,救了别人日后自家可能会赔上一命,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搭救。
[NextPage东江水与县城人]
东江水与县城人
老城内原来水井不多,数量估计应在20口左右,多属私人或某姓氏宗人所用(如韩氏古井),而且井水量受季节影响较大,远不能满足城内居民的用水需要。自古以来到江边担水和浣衣成了人们的生活规律。1961年在葫芦岭顶建造了自来水厂(今自来水公司第一水厂),虽然每条巷弄中仅设有一只水龙头(专人收费,每担水收费1分),居民到江边担水日见稀少。
80年代以前,每年逢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居民有在天亮之前到江边担水的习俗,并将江水用坛罐密封贮藏以备用。据说“七夕水”有特殊功效,长年贮而不腐,可配以“叶上开花”(一种中草药)或木棉花等治疗刀伤、火烫或疮疖。成年人在趁早去担水时,会叫醒家中小孩同往江边,让小孩在江边游泳或泡身,以防盛夏生疮疖痱子。
农历七月十四俗称“水鬼节”,每家每户还是会张罗加菜过节。不过大人会告诫小孩,水鬼节不准到大江游水,免得被海龙王招走。然而,并不是所有小孩都乖乖听话,当年我就有过在水鬼节偷偷去大江游水的经历。
南人乐泳,限于县城內的小游泳池早已废弃(旧址在今县博物馆),东江两岸成了县城居民的天然浴场。每到夏天泳客络绎不绝,横水渡生意红火,泳客人数之众,至90年代初,甚至到了要动用公安水上派出所维持安全秩序的程度。
不过话得说回来,在80年代以前生活条件艰苦的岁月里,成年人并没有多少“游兴”,父亲把儿子教会了游泳便算有了交待。小孩基本上是由父兄、伙伴教会了游泳。
以前人们的安全意识不强,对小孩疏于约束。夏天中午至黄昏,江面上小孩三五成群尽情嬉玩,胆大的干脆结伴渡江。记得我在一小读一年级时上体育课,老师竟敢带着全班四十多名学生到博中码头游泳,善泳的昼疍家同学竟游到江心!换上如今,给个天让老师做胆也不敢这样做,家长也一万个不答应。
俗语有讲:欺山莫欺水。这句话我从小没有少听,但面对畅泳东江的诱惑,就将大人的叮嘱当“唱歌”了,一条小命几乎扔在江中。除非生病,大人允许也去游,不允许就偷偷去游;好天去游,下雨也去游;平日去游,洪讯、“水鬼节”也去游,甚至是渡江。我第一次横渡东江大概是在十二三岁的年纪。一次,江水已漫上对面水堤坣(江面宽约四百米),我和几个邻家男孩从博中码头下水,一路被江水漂打游了一公里多的河段,在离岸还有几十米时,我忽然脚部抽筋。一个念头在脑海一闪:这回完蛋了!随身没有救生物,小伙伴已被江水冲散。我没有呼救,下意识地将一只脚伸直,竟然着脚(对面水岸边沙多平缓)!!!小命不该绝。。。
初中毕业那年整个暑期,我与十多个同学几乎天天渡江,从北岸下水游到对面水,再从对面水免费坐横水渡到北岸客运码头(到对面水只卖往程票,返程不收费)。在渡船即将靠岸之际,我们十几个同学一齐跳江,顺流再游几百米到住在江边的县木材公司的同学家中换上衣服。
印象中的东江上的盛事,不是龙舟竞渡,也不是近年来的春节烟花汇演,而是70年代初的一次政治性活动。其时毛泽东以年近八十的高龄横渡长江,一时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游江湖海的热潮。那年,县城的干部职工群众、工农商学兵代表多达两三千人,在博中码头下水,簇拥着大书上“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等大型木制标语牌,解放军官兵和民兵还背着步枪,游江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的游到水西造船厂码头上岸。城中一时空巷,群众驻足在江边或堤围坣上一睹盛况。
东江依旧无语西流。。。她哺育了世代东江儿女,也见证了沧海桑田,世事变幻。
[NextPage葫芦岭]
葫芦岭
在介绍葫芦岭之前,先贴上一篇N年写下的日记:
2月8日 星期天 阴雨
睡到中午1点方起,老婆孩子早吃饱了。
刚起床我一向胃欲不振,泡了一壶铁观音,点燃了一支香烟,总算有点惬意的感受。还是上网、听歌......
不觉已过3点,肚子里诸葛亮焚香端坐城头弹琴,老婆带女儿到学校注册去了。我如单身寡仔,唯有外出弄点吃的。一个人冒着寒冷细雨走在大街上,在一间小食店內坐了下来,叫来一碗馄饨面、两只盐焗蛋,也足够顶肚了。
肚饱之余又感百无聊赖,上哪去呢?!上山去,去回味久违的雨中登高赏雨景的感觉。
博罗人惯称的葫芦岭,县志上称为浮碇岗,一座仅仅六七十米的风化石小山岗。传说当年铁拐李赴南海途中,在云端上俯视着被洪魔肆虐着东江的民众,乃抛下随身的葫芦,化为一座状似葫芦的山岗,灾民得以劫后余生。如今已辟为葫芦岭公园。
微雨中,我轻步拾石级而上,时而低首看着那一块块几十年来被游人足迹磨得平滑的花岗岩石级,不由忆起在此经历过的童趣,折树杈、捉蜻蜓、摘山稔果、点着松脂钻山中的防空洞(6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昨天上午,我在一座山上足足站立了四个钟头,饱受了寒风凛雨的洗礼,由于目的不一样,心境绝然不同。
不觉已登近岗顶,竟传来一曲耳熟能详的《友谊天长地久》的音乐……我心里一阵惊喜,不!是一阵感动,一种不期而遇的心灵呼应啊!自己雨中赏景的心境,怎及得上人家雨中奏乐传情的境界啊?!我快步级上了岗顶,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危塔下,见一个神情落魄、外乡人装束的中年汉子,手捧着一具萨克斯风管,对着粘在塔壁上的《友谊天长地久》、《回家》等手抄的乐谱在不停吹奏,对我走近视若无睹。唉!又是一个未能回家与亲友团聚的异乡之客,借奏曲一抒思乡念亲情怀。我赏曲的雅兴顿失,感动荡然无存,换作一丝莫名的心酸。
岭顶上,整个县城一览无遗。南坡下的中学母校不复当年旧模样,学校还未到开学,亦不闻朗朗读书声。校前是那条正值枯水期的东江,窄浅得几乎可以趟水而过。儿时每逢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必由大人带着,赶在天亮前在江中泡身。据说,“七夕水”是“仙水”,小孩泡过不生痱子。我还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经常与小伙伴渡江,就算是农历七月十四传统的“鬼节”亦不作避忌,汛期三四百多米的江面,要游到南岸,少说得在水中漂打一个公里的水路。罢啦罢啦!不提当年勇了。江上己不见客货船争流,我平日时登江边小艇,买些肉嫩味鲜的江鱼。水上人家己所剩无几,心想不可再奢望去品味水上青年男女在晚霞江上互对“咸水歌”的乐趣了。江岸上抽沙的痕迹随处可见,惨不忍睹矣!远处江面一桥飞架南此,旧时渡船缈无影踪,更别说去找到当年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的旧战场遗迹了。江山易改啊!秉性呢?!
东面的旧城区巷陌交错,青少年一辈己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下榻过的书院(我小学母校的前身)和苏联随军军事顾问在古榕树下向民众发表打倒军阀陈炯明的革命演说。矮小寒怆的砖瓦房依旧,我是在旧城区出生长大的,度过了16年的少年时光。1938年10月日寇在城内狂轰滥炸,外公的房子变成残垣败瓦,又无力重建,自始祖孙三代唯有长年租公产房栖身。我的目光极力去寻觅着曾经居住过的三条小巷弄,百般往事一时涌上心头。转身放眼北边新城区,在那杂乱无章的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中,不似辩寻小巷那般费神,我现住的一幢N层“豪宅”相当显眼,熟悉而陌生,红黄间衬的外墙瓷砖,竟不及青砖灰瓦有亲切感。
看过远景,我开始留意些细微的东西。看着树上钉上的标识,我才知道与自已一同在风雨中成长的树木的学名叫台湾相思,又叫相思柳……太诗意了吧?相思风雨中?!嘿嘿!我心里几声苦笑。塔壁上、护栏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写满了痴情男女留下的“爱你一万年”、“爱老虎油”诸如此类的爱情宣言,有的还留下了QQ号码。与当年几乎千篇一律“某某到此一游”的“题辞”,似乎更多了些“浪漫情调”。
在山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一个钟头快过去了,我终于沿着东面山坡的公路缓步下山了。行至山脚时,留意着儿时无数次进出过的狭矮的防空洞口,洞口早己被石块水泥封死了。是啊!我们还能让子女再进去“寻幽探胜”吗?!山脚护坡墙上堆砌着的粗厚、长满青苔的古青砖块,我听妈妈说过,是他们那一辈的人年轻时从旧城墙拆卸下来用作修筑葫芦岭的。就是这些墙砖,已成为这座早在秦代设县制的千年古城难得的历史证物了。山脚下有“东岳宫”、“南海观音堂”等寺庙,门前善信正在上香祈福。佛教是泊来品,从天竺传入中土,始盛于魏晋。但国人信佛,趋福避祸的功利心太重了。我虽不信神鬼,还是在庵前驻足。庵门的石楹上镌有一联,上联:观修净业登彼岸;下联:音响圆融趣菩提。橫披:慈云法雨。我有心录下,幸随身带有一支钢笔,从口袋里搜出一张出门时缴交手机话费的收据,垫在膝盖上抄了来。却因钢笔书写不畅,我竟在观音堂门前抓着钢笔挥手甩了几下,浅浅的积水消融着黑笔水……罪过!竟玷污了佛门圣地。于是,我怀着负罪感步入了观音堂。在观音娘娘的慈颜之下,我没有上香,没有躬身作揖,也没有祈求宽恕,只是在若有所悟地凝视着……堂内侧屋的几个头结发髻的老太太似乎不太留意我,一直在忙碌着。我走时,悄然往善德箱塞进了香油钱……
神佛若有灵,容我祈祷一回,保佑芸芸众生吧!